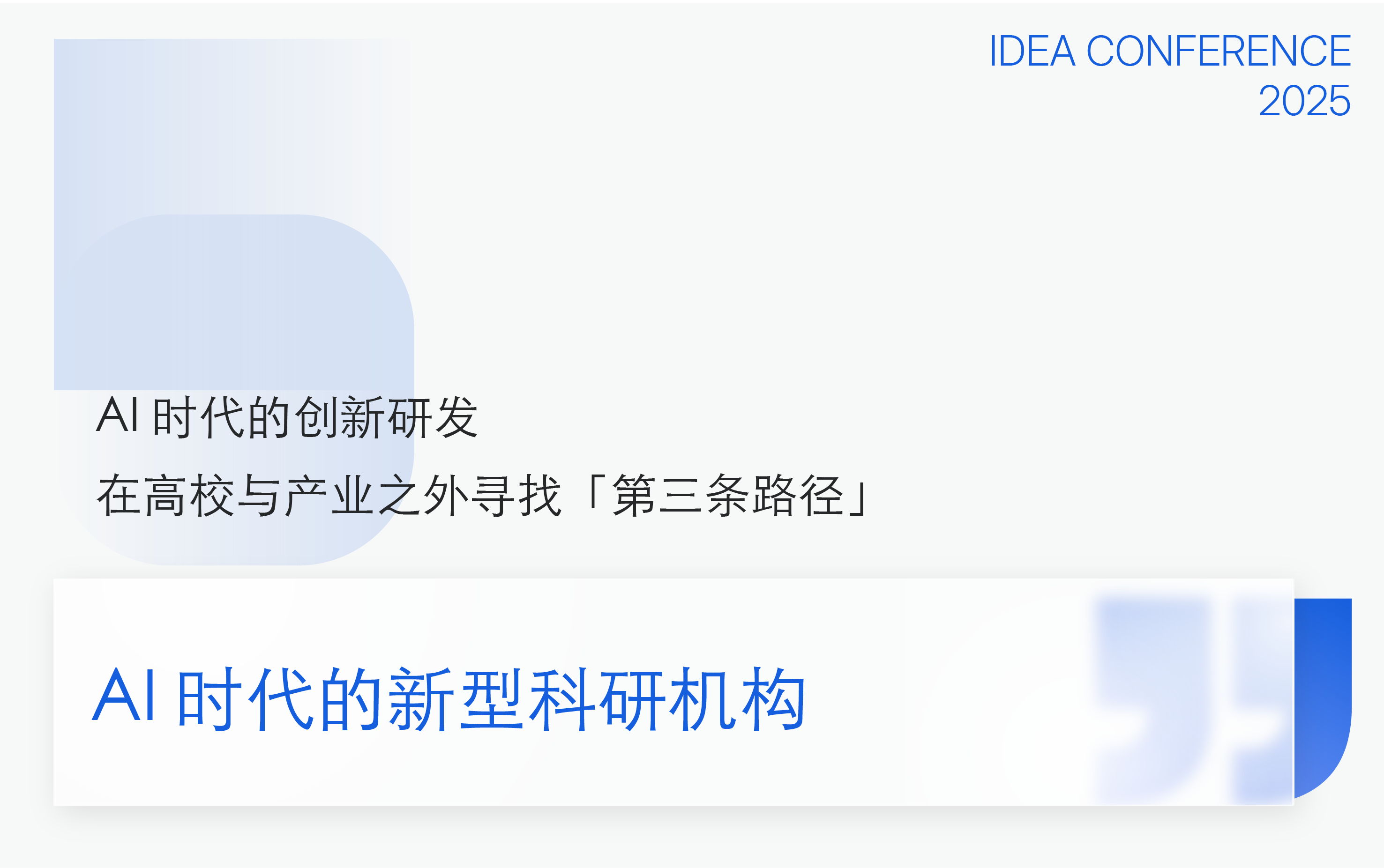
圆桌主持
IDEA 研究院副院长、首席科学家,深港高等研究交流中心负责人 郑立中
圆桌嘉宾
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长聘教授、系主任 汪玉
香港科技大学(广州)信息枢纽院长 陈雷
光明实验室主任,华为终端 BG 首席科学家 田奇
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谢源

新型研究机构
该如何定位评价
长期以来,顶尖高校被视作科研方向的“领队者”,但在 AI 的推动下,这一格局正在动摇,科技巨头企业开始产出突破性创新成果,大学与产业界的科研边界开始变得模糊。
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改变科研生产方式的当下,AI 时代的科研究竟由谁来领队? 传统高校、企业研究院与新型研发机构之间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,背后的定位与评价机制,正成为科研体系能否迈向下一阶段的变量。
汪玉以负责的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为例,讲述了新型机构的运行逻辑。该研究院成立于 2015 年,本质上承担清华科研成果转化和对外合作的职能,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基础研究机构。“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吸引最好的人才。给不出最高薪水,又要承受激烈的市场竞争。”他说,因此他们尝试采用“小公司式方式”来孵化团队,让人才在市场环境中成长,同时将学校的科研成果推向市场,扩大影响力。他认为,只靠政府投入,不可能长期干好一个研究院,学校、政府、产业,这三重力量必须融合起来,才能形成可持续的机制。”
陈雷认为,在 AI 时代,既要基础研究、又要产业结合、还要影响力,新型机构需要让年轻人看到这种路径是可行的。“不能说我做基础学科,你给我五年,我憋个大招。五年之后憋不出来怎么办?所以我们提倡‘沿途下蛋’,持续产生成果。”他举例,最近与华为讨论的大模型“数据投毒与污染问题”,既有研究深度,又有产业急迫性,而这类课题在传统高校体系中往往无法被充分覆盖。“既要又要还要”,成为对科研机制的必然要求。
田奇指出,在 1990 年代,一个人、一台 PC 就能完成博士阶段的全部研究,但在今天,AI 已经是一种小团队协作的工程系统,科研范式发生了根本变化。在高校体系中,论文、项目、人才称号仍是主要指标,企业则更看重收入与商业结果。新型研发机构的价值,不是复制任何一方,而是补位。“能不能出现一个现象级成果——DeepSeek、ChatGPT 这样的?这才是新机构应该努力的方向。”田奇强调,新机构应聚焦于根技术的突破,这类成果可能无法立刻变现,但其科研价值和产业带动力远大于传统成果指标。在他看来,一个成功的新型研发机构应具备高校的自由创新能力、企业的工程资源,以及开源生态的开放性。三者结合,才能形成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新科研模式。
谢源将新型机构的本质总结为“桥梁”。“高校可以 Research for fun,完全兴趣驱动;企业必须 Research for profit,明确产品导向。新型研发机构要在两者之间解决‘达尔文死海’的问题。”他提出新机构的评价体系应包含三个维度:学术影响力(深度),技术影响力(对产业的贡献与传播广度),产业与社会价值(实际创造的效益或能力)。不同阶段权重不同,但三维结构需要共存。
新型研究机构
新型组织形式
AI 时代的新型科研机构究竟应如何组织?传统大学依托院系体系,优势在于积累深厚、体系完整,但在跨学科研究上往往显得僵硬;企业以项目和产品为中心,路径明确,却容易形成“团队壁垒”,在学术深度和长期投入上存在不足。在学科为基础和项目为基础的两种方式之间,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?
汪玉指出,在清华电子系的长期实践中,一个清晰的趋势是科研组织正向“中台+小团队”演化。他形容这种结构像一个共享的大平台,“我们会有一条线叫厨房,老师们或小团队是厨师,做出菜来”。底层平台需要系统性投入,而各团队则围绕具体需求灵活创新,这种模式在 AI 时代尤其重要,因为平台化能力正在成为跨方向协同的基础。
跨学科组织方式被视为打破传统架构的另一条路径,陈雷举例说,港科大(广州)距离刻意让教师坐得“乱七八糟”,计算机、材料、生命科学的办公室混合排布,物理空间先行打破边界。资源配置上,钱不是给老师,而是给学生,学生依据兴趣组建跨学科团队,再反过来吸引导师加入。例如在碳中和方向,一个学生团队可能同时需要环境、材料和计算机多位老师的支撑,这迫使教师跨界合作。他强调,这种机制让跨学科团队“自然长出来”,而不是自上而下被组织出来。
田奇指出,高校“兴趣驱动、方向发散”,企业则是“商业变现驱动”,但新型机构需要第三种路径——愿景驱动。他提到光明实验室正在探索一种“1 变 3、3 变 9、9 合 1”的组织方式,即从一个明确愿景出发,通过拆解成多个模块形成“乐高式”组合,保持协同,推动从底层技术到系统应用的整体进展。
谢源以芯片设计流程为例,将其拆分为三个维度:一是由架构、设计、验证等构成的能力中心;二是 CPU、GPU 等面向具体目标的项目团队;三是所有项目共享的技术平台。“为了设计一颗 GPU,需要能力中心+项目团队+平台一起协同”,他指出,这种既专业又灵活的模式有助于解决大规模复杂工程的组织挑战,也为新型科研机构提供了结构参考。
新型研究机构
钱从哪儿来
如何让科研在不确定性中持续推进,是所有研究机构面临的难题。郑立中提出,研究往往充满不确定性,问题 A 做不出来,问题 B 虽有进展却难以盈利,机构资金如何保障这些探索?
嘉宾们普遍认为,机构资金来源应当多元,获得政府支持的同时,也要积极吸引市场资金支持,例如大型企业或风投参与。另外,研究闭环与盈利闭环不宜强耦合,保留小比例项目自由探索,大比例项目有目标方向,保证创新空间,也维持一定产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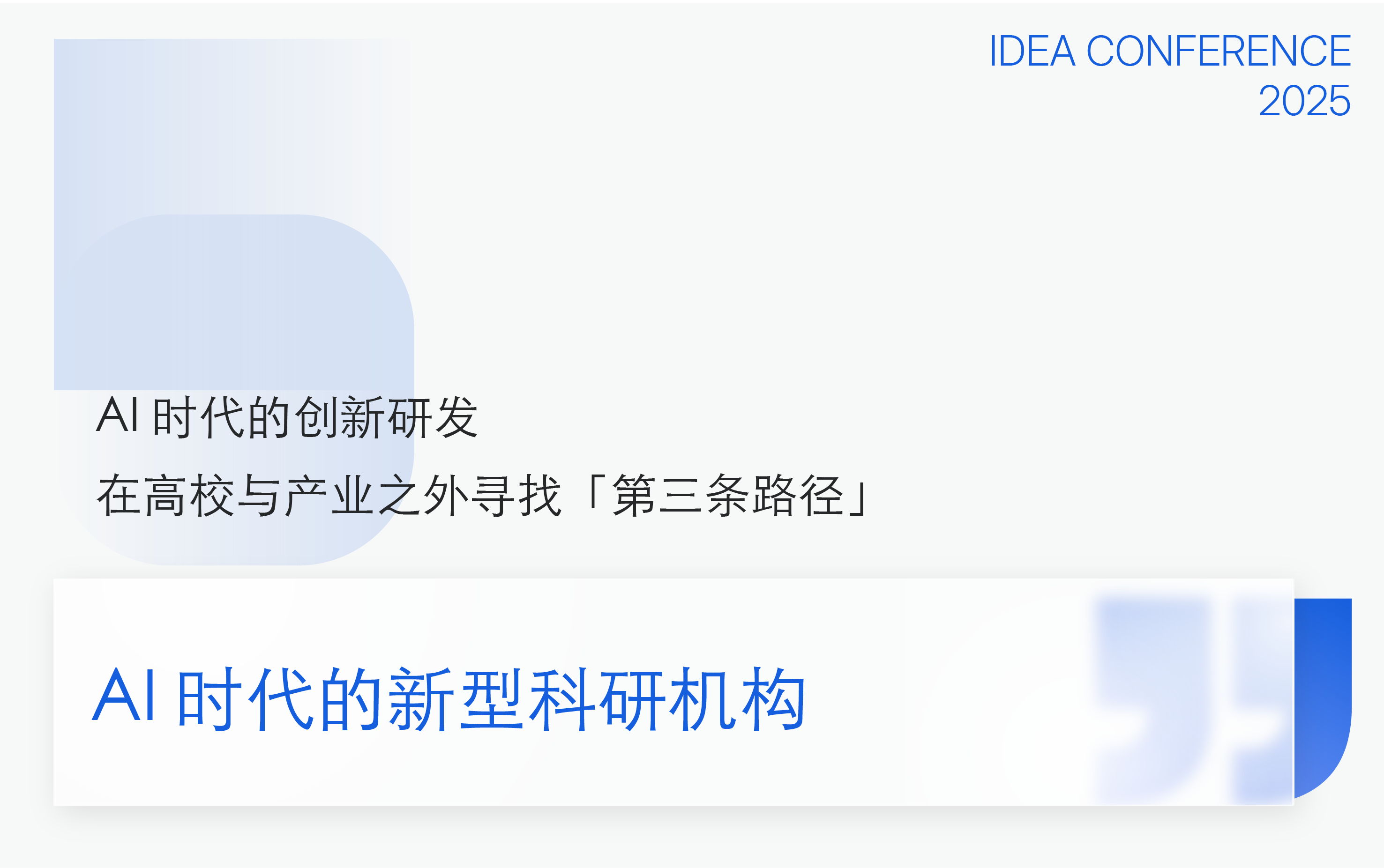
圆桌主持
IDEA 研究院副院长、首席科学家,深港高等研究交流中心负责人 郑立中
圆桌嘉宾
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长聘教授、系主任 汪玉
香港科技大学(广州)信息枢纽院长 陈雷
光明实验室主任,华为终端 BG 首席科学家 田奇
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谢源

新型研究机构
该如何定位评价
长期以来,顶尖高校被视作科研方向的“领队者”,但在 AI 的推动下,这一格局正在动摇,科技巨头企业开始产出突破性创新成果,大学与产业界的科研边界开始变得模糊。
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加速改变科研生产方式的当下,AI 时代的科研究竟由谁来领队? 传统高校、企业研究院与新型研发机构之间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,背后的定位与评价机制,正成为科研体系能否迈向下一阶段的变量。
汪玉以负责的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为例,讲述了新型机构的运行逻辑。该研究院成立于 2015 年,本质上承担清华科研成果转化和对外合作的职能,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基础研究机构。“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吸引最好的人才。给不出最高薪水,又要承受激烈的市场竞争。”他说,因此他们尝试采用“小公司式方式”来孵化团队,让人才在市场环境中成长,同时将学校的科研成果推向市场,扩大影响力。他认为,只靠政府投入,不可能长期干好一个研究院,学校、政府、产业,这三重力量必须融合起来,才能形成可持续的机制。”
陈雷认为,在 AI 时代,既要基础研究、又要产业结合、还要影响力,新型机构需要让年轻人看到这种路径是可行的。“不能说我做基础学科,你给我五年,我憋个大招。五年之后憋不出来怎么办?所以我们提倡‘沿途下蛋’,持续产生成果。”他举例,最近与华为讨论的大模型“数据投毒与污染问题”,既有研究深度,又有产业急迫性,而这类课题在传统高校体系中往往无法被充分覆盖。“既要又要还要”,成为对科研机制的必然要求。
田奇指出,在 1990 年代,一个人、一台 PC 就能完成博士阶段的全部研究,但在今天,AI 已经是一种小团队协作的工程系统,科研范式发生了根本变化。在高校体系中,论文、项目、人才称号仍是主要指标,企业则更看重收入与商业结果。新型研发机构的价值,不是复制任何一方,而是补位。“能不能出现一个现象级成果——DeepSeek、ChatGPT 这样的?这才是新机构应该努力的方向。”田奇强调,新机构应聚焦于根技术的突破,这类成果可能无法立刻变现,但其科研价值和产业带动力远大于传统成果指标。在他看来,一个成功的新型研发机构应具备高校的自由创新能力、企业的工程资源,以及开源生态的开放性。三者结合,才能形成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新科研模式。
谢源将新型机构的本质总结为“桥梁”。“高校可以 Research for fun,完全兴趣驱动;企业必须 Research for profit,明确产品导向。新型研发机构要在两者之间解决‘达尔文死海’的问题。”他提出新机构的评价体系应包含三个维度:学术影响力(深度),技术影响力(对产业的贡献与传播广度),产业与社会价值(实际创造的效益或能力)。不同阶段权重不同,但三维结构需要共存。
新型研究机构
新型组织形式
AI 时代的新型科研机构究竟应如何组织?传统大学依托院系体系,优势在于积累深厚、体系完整,但在跨学科研究上往往显得僵硬;企业以项目和产品为中心,路径明确,却容易形成“团队壁垒”,在学术深度和长期投入上存在不足。在学科为基础和项目为基础的两种方式之间,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?
汪玉指出,在清华电子系的长期实践中,一个清晰的趋势是科研组织正向“中台+小团队”演化。他形容这种结构像一个共享的大平台,“我们会有一条线叫厨房,老师们或小团队是厨师,做出菜来”。底层平台需要系统性投入,而各团队则围绕具体需求灵活创新,这种模式在 AI 时代尤其重要,因为平台化能力正在成为跨方向协同的基础。
跨学科组织方式被视为打破传统架构的另一条路径,陈雷举例说,港科大(广州)距离刻意让教师坐得“乱七八糟”,计算机、材料、生命科学的办公室混合排布,物理空间先行打破边界。资源配置上,钱不是给老师,而是给学生,学生依据兴趣组建跨学科团队,再反过来吸引导师加入。例如在碳中和方向,一个学生团队可能同时需要环境、材料和计算机多位老师的支撑,这迫使教师跨界合作。他强调,这种机制让跨学科团队“自然长出来”,而不是自上而下被组织出来。
田奇指出,高校“兴趣驱动、方向发散”,企业则是“商业变现驱动”,但新型机构需要第三种路径——愿景驱动。他提到光明实验室正在探索一种“1 变 3、3 变 9、9 合 1”的组织方式,即从一个明确愿景出发,通过拆解成多个模块形成“乐高式”组合,保持协同,推动从底层技术到系统应用的整体进展。
谢源以芯片设计流程为例,将其拆分为三个维度:一是由架构、设计、验证等构成的能力中心;二是 CPU、GPU 等面向具体目标的项目团队;三是所有项目共享的技术平台。“为了设计一颗 GPU,需要能力中心+项目团队+平台一起协同”,他指出,这种既专业又灵活的模式有助于解决大规模复杂工程的组织挑战,也为新型科研机构提供了结构参考。
新型研究机构
钱从哪儿来
如何让科研在不确定性中持续推进,是所有研究机构面临的难题。郑立中提出,研究往往充满不确定性,问题 A 做不出来,问题 B 虽有进展却难以盈利,机构资金如何保障这些探索?
嘉宾们普遍认为,机构资金来源应当多元,获得政府支持的同时,也要积极吸引市场资金支持,例如大型企业或风投参与。另外,研究闭环与盈利闭环不宜强耦合,保留小比例项目自由探索,大比例项目有目标方向,保证创新空间,也维持一定产出。
